 |
|
勞麗麗在生活館與公眾進行有機食物工作坊。照片由Andy Wong拍攝,由「一小步,行在地上」提供。 |
 |
|
勞麗麗在生活館與公眾進行有機食物工作坊。照片由Andy Wong拍攝,由「一小步,行在地上」提供。 |
勞麗麗是位來自香港的藝術家,創作媒介包括錄像、攝影、裝置等。2006年,麗麗取得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主修藝術。其後任職旅遊雜誌記者,至2015年重返校園,並於2017年取得香港中文大學的藝術碩士。勞氏曾參加的個展包括《保持緘默》(Tommorrow Maybe,2019)、《欲壑難填》(本來畫廊,2018)、《漫慢電視— 安.伊莉亞森的凝視》(據點。句號,2016) 、《記念品與禮物》 (觀察社,2014)等。她曾參與的群展包括德國 OSTRALE 019 雙年展、《今天應該很高興》(北京泰康空間,2018)、《魚塘源野藝術節》(香港元朗大生圍,2018)、《香港農民曆》(Spring工作室,2015)等。她為香港 WMA 委託計劃「機遇」得主(2018-19),作品《飛天潛水艇》入圍香港第二十三屆ifva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公開組」。作品同時獲The Sigg Collection收藏。
勞麗麗以「半農半X」形容自己的生活方式,專注與大自然生態有關的藝術創作。「半農半X (はんはたはんX)」這概念來自日本。 90年代的時候,日本的塩見直紀觀察到生活與城市的矛盾,於是他提出與自然建立多一點關係的生活方法。「你可以說這生活方式是理想而自由的,但其實很難實踐到,譬如說是時間上的分配,過程中會有很多矛盾。雖然如此,但我認為這是『半農』與『半X』之間的一個提問。『X』其實是你耕作以外的天賦,問題是你如何實踐一個互補的、互成影響的生活習慣。」[1] 麗麗在一次座談會上分享對「半農半X」的理解。在另一篇關於麗麗的文章,作家鄧小樺進一步補充了關於「互補」的關係:「她在田間,本不是持藝術家身份,本來沒有打算把生活經驗變成創作。只是在田間,工作生活久了,『自然而然想紀錄耕田時放空的狀態,以及勞動的狀態』,於是她把一些手攜式攝錄裝置,放置在田間,積而久之就有了大量的毛片(footage),這可算巨大的資料庫,記錄了土地的變化。」[2]
也可以說,麗麗的藝術不一定是關於耕作的,她並不是單純的「因為創作所以耕作」,亦不是「因為耕作所以創作」。相反,她關心的是如何與自然建立關係。耕作是她的生活方式、創作是她的溝通方法。這次研究團隊紀錄了勞麗麗的幾份創作,一看她耕作和創作之間的互動。
 |
|
生活館。照片由生活館提供。 |
2005,香港政府開始規劃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高鐵),當中最受爭議的議題包括遷拆菜園村。高鐵工程收地範圍為27公頃,當中有大約4公頃為菜園村。2008年,政府在沒有諮詢居民的情況下對菜園村發出清拆令,當時有不同文化工作者、社運人士、藝術家等等組織了生活館,他們學習耕作、練習耕作,以農田實踐回應那時候菜園村的遭遇。而勞麗麗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接觸耕作的。「當時那個方案令我們這群在城市裡住的年輕人心裡不舒服。即使如此,我們也做不了什麼,我們只是覺得有些郊區自然的東西要保護起來,不過我們是沒有種田經驗的。」麗麗在訪談裡說。於是,她和朋友開始向老師學習種田,她的老師曾說:「你去學習這是怎麼一回事,才會知道耕作的好與困難。」也就是說,要通過身體的實踐才能真正體會自己與土地的關係。最終在2010年1月,立法會通過了超過600億高鐵撥款,而整個高鐵也正式在2018年啟用,當時部分的菜園村村民搬到新菜園村去,勞麗麗和她的朋友繼續生活館的耕作生活,務農的工作包括鋤田翻土、培苖、堆肥、灌溉、防治或處理蟲害、收割、銷售等環節。
2015年,麗麗參與了藝術空間Spring 工作室的「香港農民曆」,她設計了一塊風呂敷,一式共兩款顏色,湖水藍和薄荷綠,上面印有插秧、除草、施肥等八十八個種米步驟,希望用家以這布來包裹餐盒的時候會想起米粒的來源。
 |
|
「香港農民曆」風呂敷 |
她在2015年再一次回到藝術學院以後,創作了《再會吧 香港》,影片一邊放著藝術家黃衍仁創作的音樂,以卡拉OK一樣的方式呈現歌詞,另一邊拍攝歌詞的手語翻譯,並在影片中加插在高鐵地盤前耕種的畫面。「那抗爭的歌曲竟在不同年代通行,我們何時能再會?」這是麗麗對這作品的註腳。
《再會吧 香港》
2016-17 / 8'35" / 高清單頻道錄像
「社會運動對某些人的影響可近乎零,但卻可能對某一小撮人是翻天覆地的人生轉捩點。『反高鐵、護菜園』的運動對我及一班朋友,是重大的改變,對於我來說,那是我首次投入參與的運動,雖不是什麼前線,在現今時局看來更是『和理非』得很。『千人怒撐菜園村』、萬人圍立法會、巡守隊護村的場面在當年已相當震撼,但我在其中參與,不免會對個人身份猶豫,我該存在甚麼位置呢?我們必定要叫同一句口號嗎? 群體感染力甚強,我是同樣在同一個頻率躍動起來,但在運動現場,不免二元對立。運動過後,我們何去何從?」[3] 麗麗在一篇與Para Site策展人瞿暢的對談裡說。
在經歷了好幾年的社會運動後,麗麗重返學院,開始整合以前的經驗和想法,並發展屬於自己的藝術語言。她特別對論文式電影感興趣,「我喜歡文字。在種田時好,旅行時也好,我也會拍下一些鏡頭。拍的時候我沒有想把它們聯繫起來,這也是我最自然的創作狀態。過了一段時間,我會把這些片段翻出來,再看怎麼把作品做出來,這是我創作的方法。」麗麗對研究團隊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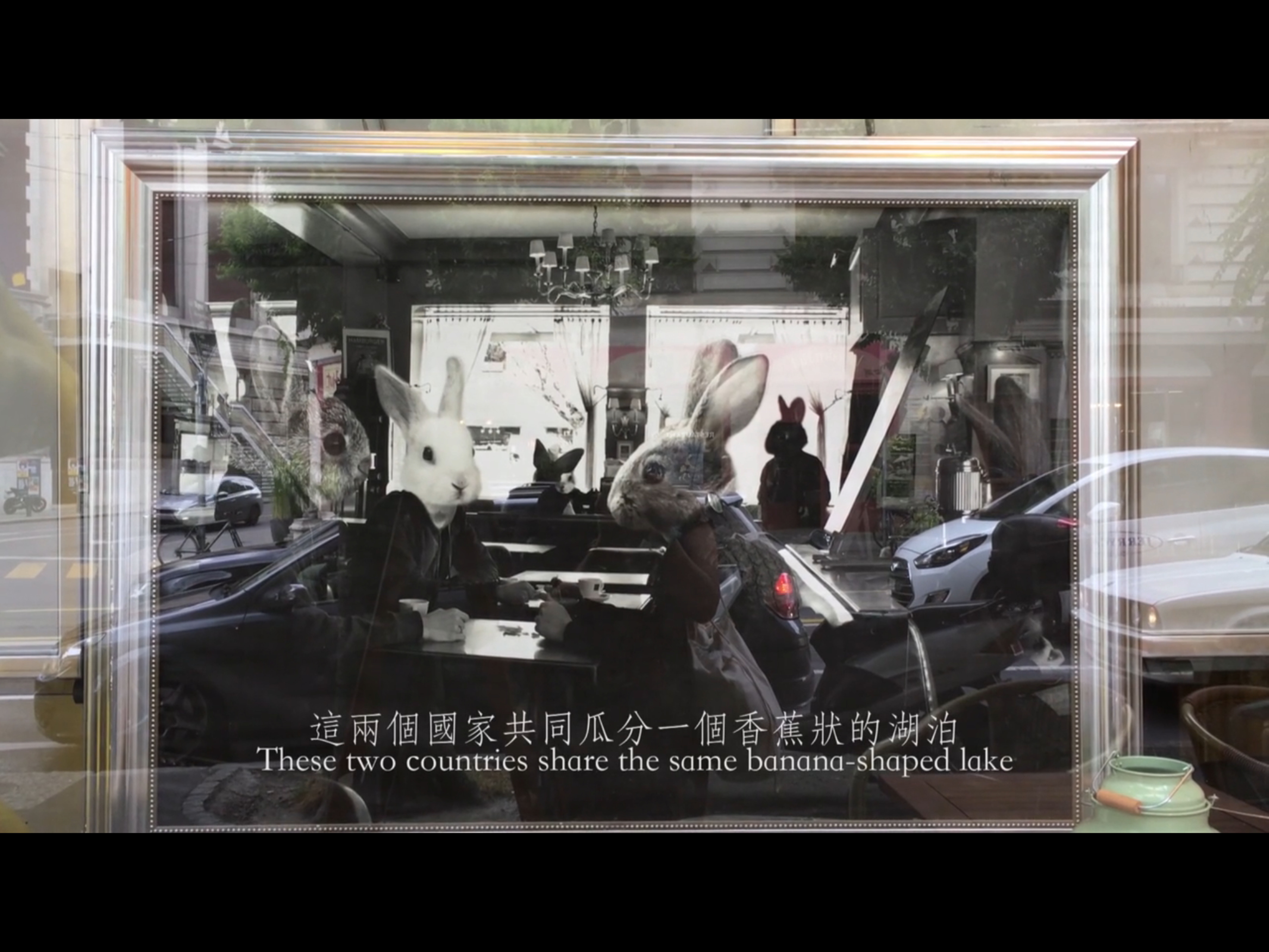 |
|
《冰川》截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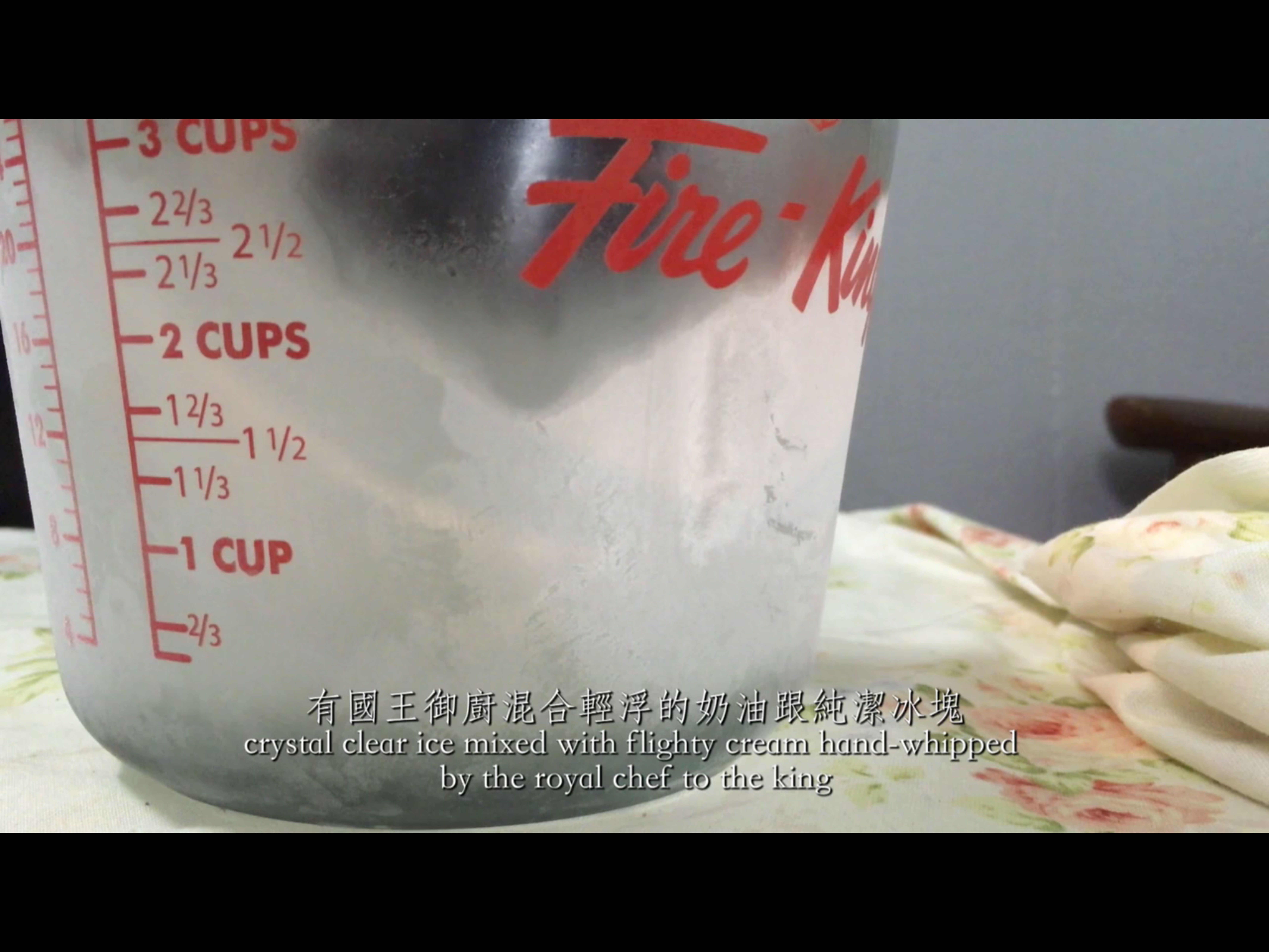 |
|
《冰川》截圖 |
 |
|
《冰川》截圖 |
|
冰川 |
冰川所說的是冰川與種田背後理想的糾結關係。影片穿插了她在瑞士旅行時一家咖啡室所拍跟香港務農時的畫面,雨中的水稻田、一片覆蓋還在生成的稻穗的防雀網、農夫收割水稻後碾穀等。影片的文字像一篇意識流散文,由對日常會議的想法開始,然後談及虛構的地方,譬如G市、香蕉湖的傳說。麗麗把「冰川」的冰與冰淇淋連想在一起,展開她對食物來源、製造,以及到人類進食的思緒。影片沒有直接提及「氣溫上升、冰川融化」等字眼,卻以藝術家的幻想和生活經驗組成了一部長達17分鐘的影片。在她於廣州本來畫廊的個展裡,麗麗更創作了冰川制作中,以氯化聚氯乙烯樹脂製造了冰淇淋溶掉中的模樣,以雕塑回應錄像。
「麗麗作品敘述的推進,並不是邏輯性的,而是靠大量的直覺、類比和想像接駁。這種關聯,綿密地出現於文字與文字、影像與影像,甚至是文字和影像之間,令作品出現不同維度,猶如在影片中編織出天空、陸地、大海三層 —— 上一秒說天的故事,下一秒躍到海的問題,但身在海中未必可以看得清海的問題,從天空看海,反而有機會看得更加清楚。」[4] 藝評人 Fizen Yuen在一篇評論文章裡描述麗麗的創作。
 |
|
《冰川制作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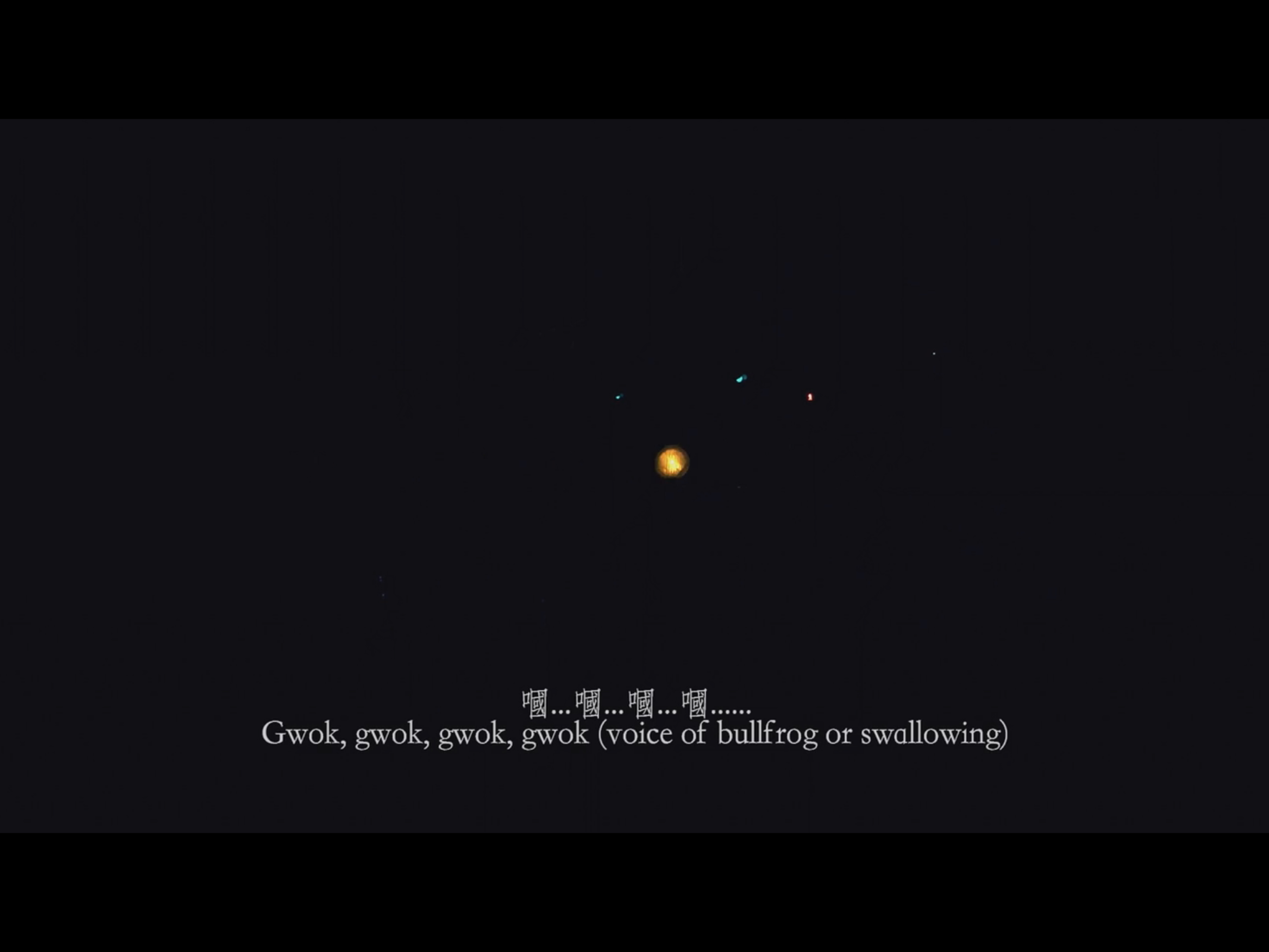 |
|
《飛天潛水艇》截圖 |
 |
|
《飛天潛水艇》截圖 |
 |
|
《飛天潛水艇》截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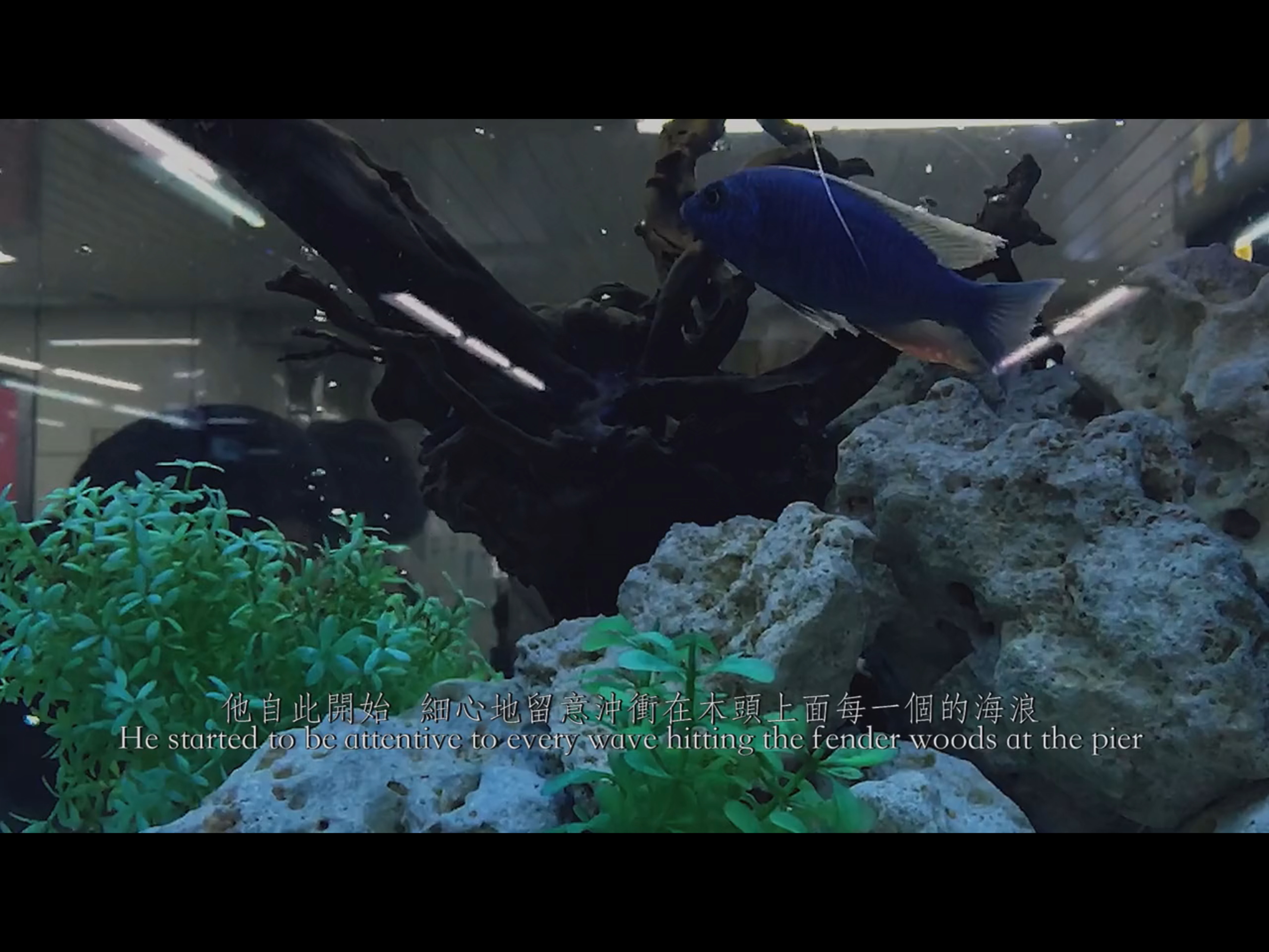 |
|
《飛天潛水艇》截圖 |
《飛天潛水艇》
2017 / 彩色 / 9’20”/ 單頻道錄像 / 中英文字幕 / 雙聲道
「大自然中的她化作飛天潛水艇,來者不拒,多年來運送五花百門的物事,包括欲望。」
飛天潛水艇以黑夜裡的蛙聲展開,影片拍著夜裡海上的船燈一閃一閃的,然後鏡頭一步步拍水:夜裡海水上光的倒影。文字寫:「他跟我提過/每潛下約10公尺便增加相當於一倍的大氣壓力」。藝術家以這段文字展開故事:「我有一個特別技能/可以連繫到世界每個角落/當你一覺醒來/我已經去了他方/簡單一點來說/我可以稱為最早一代的物流公司/(…) 很多客人都會來找我/運送的事物千奇百怪/甚至包括慾望」。作品裡的潛水艇並沒有特定的模樣,藝術家穿插了她在飛機上拍的天空、農田的快鏡、在泥田耕種的畫面、水族箱的養魚、收割薑的過程等等。從海水到天空,再到泥地,潛水艇不再是只出現在海裡的機械,藝術家把這機械的模樣聯想成一塊本地薑, 以近乎《小王子》裡描寫大象/帽子的邏輯理解潛水艇,打開觀眾對機器與自然之間的想像。而影片也以一句「(你究竟是誰呢?)」作結束,為作品留下讓人追問下去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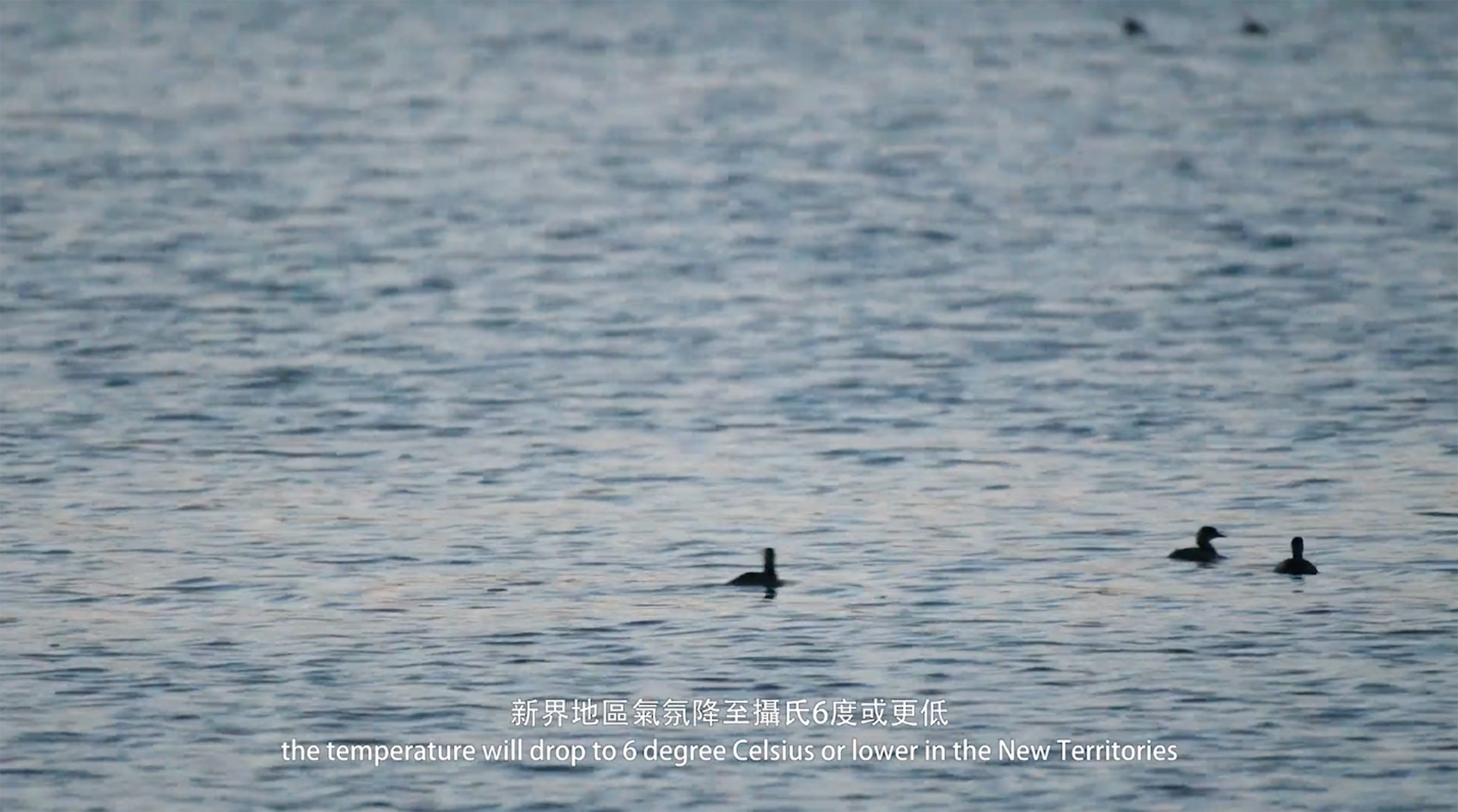 |
|
《焉知》 |
 |
|
《焉知》 |
 |
|
《焉知》 |
 |
|
《焉知》截圖 |
焉知是一部講食物鏈的作品。影片以香港元朗的水塘出發,講人類和魚之間的關係。但是,麗麗並沒有以說教的方法來說這故事,反之,藝術家在這作品表現了她看不同物種的態度,對她來說,不同物種之間生活在同一個生態裡,是應該可以互相了解、甚至溝通的,影片的敘述不是由人類為中心,也不是擬人法的從魚的角度講。影片是從一位「觀測者」的角度來說,這「觀測者」的角度並沒有偏向任何一個物種,不是想挑起人對魚的憐憫,也不是放大人類的捕獲過程。麗麗在影片裡談及所有物種都共同感受的自然條件,水、溫度、競爭等等。在影片的後段,「觀測者」說:「來訪不久後,我便發現頻道的訊號相當飄忽,雖然已開放給所有生物收聽,但通常也有人為意外,有時候可能只收聽到一到兩個頻道。起初接到投訴時,我還以為可以反映一下,但當問一下同事,才發現早就有如此情況,又可能根本沒有收聽另一個頻道。」這作品的敘事者以物種之間的「觀測者」角度出發,沒有浪漫化任何一方,更沒有故作神秘的講跨物種這概念,藝術家就以日常的語言和影像組合成另一部論文式電影。
《焉知》
2018 / 彩色 / 15’/ 單頻道錄像 / 中英文字幕 / 雙聲道
在勞麗麗2018年本來畫廊個展「欲壑難填」的座談會上,年青策展人梁皓然說:「麗麗的生活方式不只是種田,『半農』與『半X』的實踐其實改變了她觀察身邊事物的方法,她再以這屬於自己的節奏與眼光看事物,是一種已經內化的角度,所以她不是以城市人角度關注農鄉生活,也不用在作品裡強調自己是農夫的身分。對麗麗來說,城市和農田不是對立的。」[5]這也是麗麗的藝術的獨特之處,不賣弄對農鄉生活的假浪漫,而是慢慢的以生活拍下來的不同片段編織成一部接一部的作品,而當中的情緒是冷靜而輕巧的,正如藝術家何倩彤寫麗麗:「麗麗作品中的情緒總是輕輕,她更以『冷酷』來形容自己的作品。」[6]
連結
-藝術家網站: lolailai.com
-歡迎透過連結,觀賞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好想藝術》-自作業[勞麗麗:論文式電影];時間:2"56-11"19,03/06/2018,版權屬於香港電台。
© 除了特別註明外,所有照片版權均屬勞麗麗所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