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一棵树”在新疆哈密风区 |
 |
|
“一棵树”在新疆哈密风区 |
从2012年5月4日到9月16日,萨子背着一棵树徒步、露宿,从北京走到新疆乌鲁木齐,一共走了大概3800公里,全程没有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他每隔7天休整住宿1天或2天,进行洗衣、充电、整理图片文字等工作。
萨子1975年出生于新疆木垒天山脚下,新疆是他的故乡,但“一棵树”不只是一场返乡之旅。“一棵树”是萨子流浪生活的精神写照,其核心是“底层生长”。包含着萨子对身体治疗、修复的诉求。萨子1999年8月大学毕业来北京求艺。那年正值50周年国庆,外地人口遭到清查,萨子和他当时的妻子小丽得知消息后提前逃往天津朋友家,在天津美院附近生活、创作了两年,于2001年回到新疆。在之后的几年里,萨子先后来到上海、北京,期间因实施行为遭到反复罚款和干扰等原因,几次被迫返回新疆。频繁的搬家、动荡的生活让萨子与小丽的感情破裂了。2007年,萨子再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在宋庄扎下来。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在这期间发生很大变化。在大学毕业后的10多年流浪期里,家人没有太干涉萨子的生活,觉得只要他喜欢的话出去闯闯也不错。后来萨子定居北京,父母过来,看到儿子的生活看上去如此潦倒感到很焦虑,过了几年才渐渐理解,也开始支持儿子的创作,还觉得能够锻炼身体。萨子称2012年前为自己的“黑暗时期”,身体极度消耗,睡眠困难,创作状态没日没夜,身体差到了极点。生活、艺术创作等各方面的边缘经历让萨子的归乡之路赋予强烈的修行和自我救赎意味。
 |
|
小时候萨子家里养了70只羊和30多头牛,放牧是萨子的主要生活之一 |
 |
|
萨子的家乡坐落在天山脚下,他记忆中小时候的家乡冬季很冷,常常零下30多度 |
“背负”是萨子持续的创作方法——他曾背过与妻子等重的砖头在宋庄画家村大街小巷游走,以此纪念他们的感情。在整体上思考作品和自己生活的关系时,他认为砖只是他个人经历的一个剖面,对于观者来说可能有一种强迫感,而一棵常见的、生命力顽强的树,能将个人生活经历的整体性和精神性更好地表现出来。选择以树作为媒介也源自于艺术家从小在农村种地、放羊长大形成的对自然环境的亲近感,“特别是到了北京以后,希望去寻找身体、大地、和精神的归属感。”就这样,树成为萨子生命历程、生命精神的象征物。艺术家在与树的关系中投注了一种融入自然的自我暗示。在行走80多天时的一篇日记里,艺术家写道:“我似乎忘记了树的存在,就像忘记自己的身体一样。树和我成为一个整体,在茫茫的人海和戈壁中,我情愿永远变成一棵树,只是简单地存在。”
萨子背上的树是小叶黄杨。萨子说,选树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素,比如,树所需的生长条件不能太苛刻,要耐旱耐寒,生命力强。树的生长速度也不能太快,毕竟要背在身上好长一段时间,长太快就背不动了。同时,树的品种也不能太名贵,这样才能象征底层生命。小叶黄杨是北京常见的绿化品种,有一次,萨子在锻炼时见到有人植树就上前要了一棵,拿回来后先在工作室种了一个多月,然后出发时把它移植到桶里。萨子还为树桶做了特别的耐用背带。在艺术家徒步的133天间,他每天给树浇水,晚上把它放在帐篷里。到了旅途最后,他把树放在乌鲁木齐市区外的一个亲戚家里。由于受到太多关注,他不愿意提及树的具体位置。若参加展览需要使用树,他会找其他的树代替。他想好了,这棵树最终会种在自己的墓前。
 |
|
出发前树在萨子宋庄工作室的样子 |
 |
|
到达甘肃瓜州地区时树的样子 |
 |
|
晚上树放在帐篷里 |
 |
|
行走的最后一天。“背一棵树徒步,有明确的目标、方向、计划,而且‘树’背在身上是一个信念和使命。先是有一个计划性、强迫性,你必须要做,要坚持。其次户外每天都是不同的环境,有新鲜感,也会逐渐着迷。” |
自然环境是令萨子感到自在的地方,但自然环境也是凶险的,在戈壁、沙漠、风区,除了天气状况恶劣,还需要提防野狼等猛兽,经过无人区要还极有可能断粮。从五月到九月,从春天到秋天,他行走的进度也受到天气和环境的影响。天气如果太热,路面开始软化,中午和下午是没办法走的。艺术家和助手就早晨起来先走20公里左右,另一半路程在夜晚进行。从甘肃酒泉到新疆哈密基本上都要采取夜行的方式,他们带着小煤气罐和简单的厨具,和游牧民族一样生活在路上。风大的时候,过一座桥都要花去数个小时的时间。露宿的生活一开始也让艺术家不习惯,使得他在第一个月里连连生病。这些经历称不上是项目的困难,因为项目本身就包含探寻艺术家自我与外界关系的目的。
在行走前萨子早早规划好了路线,并随着行进过程随时调整,向当地人打听情况。“虽然这是一个自己提前做好的计划,但在完成的过程中,计划性是被完全遗忘的……就是走着……没想什么。刚开始,身体和终点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距离和战争感;这样‘终点’从我出发的那刻,就产生了很明确的身体反应——到达、渴望到达。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个‘终点’不存在了。”对行走的感知变化也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理念,一开始他会刻意在旅游区等具有明显地标的地方停留,对行走的方式、记录的形态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计划与想法,到后来,他不再做过多的设计,甚至刻意避开显著的地标。这可能是在今天地图随手可得、好像不存在未知的情况下,萨子行走行为的更大的意义——在强度之外的对外界环境和自我不可知的接纳。
 |
|
“房车”架构。 |
 |
|
萨子的装备很简单,包括帐篷、定制房车、备用鞋等。说是“房车”,其实也很简陋,是萨子和朋友做了基本的设计后请人焊接出来的。由于一路上的沙石里有很多汽车轮胎破裂后掉落下的钢丝,房车的自行车轮胎基本需要隔两天补一次,有时一天要补三次 |
 |
|
在戈壁荒漠扎营时,需要在帐篷底部建排水小沟 |
 |
|
2011年6月,萨子在北京沙浴口水库挖了一棵树,计划绕北京城一圈,最后将树种回原地(15天路程)。可是到了第四天,他腿部受伤,无法正常走路,惨败收场。之后艺术家开始长达10个月的锻炼准备。他每天背着石头和大米(40斤)徒步3小时以上,每天徒步12—30公里。300天的徒步训练,几乎每天萨子的妈妈都陪着他一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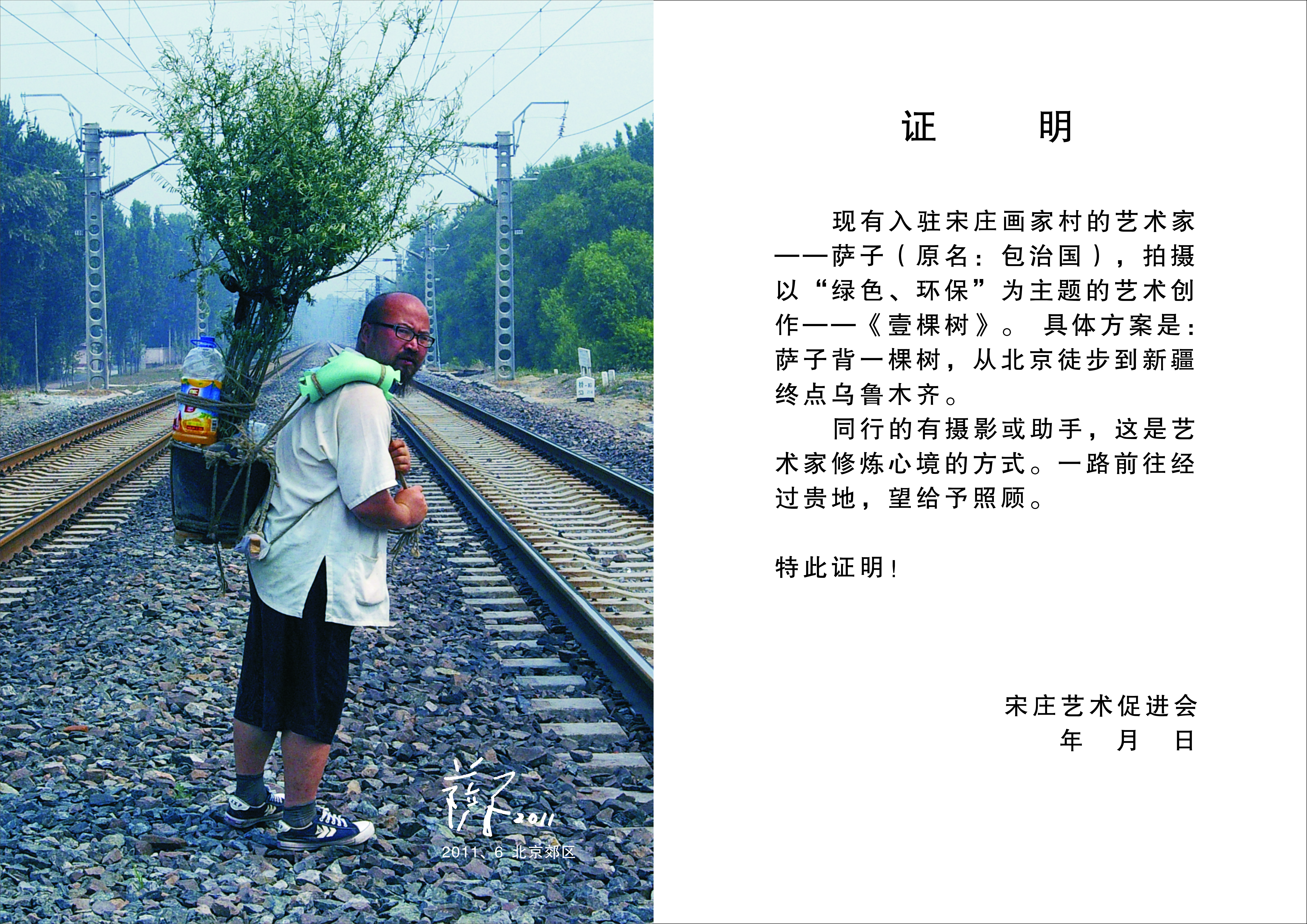 |
|
萨子准备的通行证 |
由于路途中不能时时充电,为了省电,项目的记录大多是照片,没有太多视频。照片由与萨子同行的助手拍摄。为了方便前后跑动取景,一开始助手用一辆二手的折叠小行车,后来又换了辆摩托车。萨子不会对助手的拍摄进行干预,每天上路,两人各干各的,萨子负树前行,助手跑前跑后拍摄,到了晚上两人再在一起讨论。拍摄设备很简单,要么手机,要么一台佳能400D。一开始照片效果并不好,特写和近景过多,这样很难将人物置于整体的环境中,一段时间之后拍摄的感觉才渐渐好起来:“拍这种照片和拍户外运动的照片不一样,要抓住精神性、真实性的东西和行为的鲜活特征”。
在萨子构想《一棵树》的方案时,曾有机会获得20万的赞助,条件是整个路线走佛教传教路线,一定要背菩提树,使用官方的宣传方式。萨子拒绝了赞助,卖掉几幅画,筹足三万元自费上路。《一棵树》是萨子对艺术、人生、修行的一次系统梳理和清扫:“人是悲剧性的,无法逃脱两点:一是无限的糊涂,二是无限的消耗。稀里糊涂的出生,也稀里糊涂地趟过青年时代,可是到了中年,我觉得生命还是有一点点希望——认认真真地老去,少扯些淡……艺术家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这个拯救需要切实的行动,绝非纸上谈兵。”
所有图片、视频由艺术家提供,版权归艺术家所有